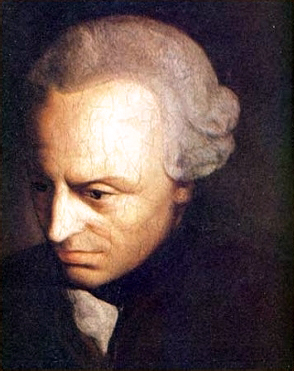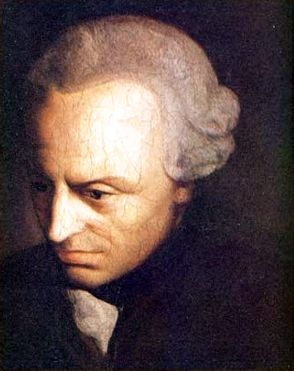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有正史和野史之分。我们相信司马迁写的,对于某些草寇写的,就将信将疑。实际上,究竟谁是谁非,谁更客观?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历史都是由人写的,都是主观的。我们之所以更相信司马迁写的,那是因为司马迁是“公认”的历史学家,他写的历史是“约定俗成”的历史,成为“历史事实”。但是,“公认”的“历史事实”并不等于就是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几百年前,地球还被西方人“公认”为是宇宙的中心呢。历史,应该说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即他们认为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批评历史学家,不是说他们在凭空挰造,质疑他们的贡献。历史学家有比较专业的研究考证方法,我们相信他们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不等于就要相信他们说的就是唯一的“事实”。要知道历史上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很多,而且这些事情很多是经过口述来传播的,先不说人心叵测,人说话都是带主观判断的,这些主观转述的事情最后辗转才到了历史学家的耳朵里,再经过他的主观的信息整理,最后才见诸笔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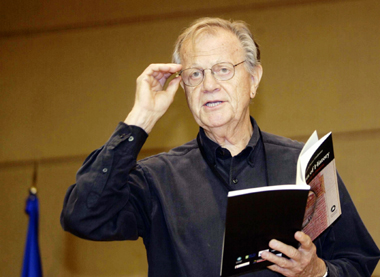 依此可见,要想知道客观真相是很不容易的。要是在太空上有一部高清晰度的摄影机,可以穿透屋顶,几千年来不差一秒地把地球人类的所有角落里的帐前幕后的行为话语都原原本本地纪录下来,那么或许可以给我们更客观的历史答案。真希望有某个热心的外星人几千年以来孜孜不倦地在干这件事情,但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收到它给我们的意外惊喜。凭历史学家的毕生精力,是不可能回原浩瀚如宇宙的历史事件、历史细节的。其实,即使有这份意外惊喜也不能完全做到客观公正地重现历史事实。要重现历史事实,除了说和做,还要了解当事人的意愿,而意愿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是有可能与言行相背离的。所以,历史,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论证,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历史事实。正是因为如此,怀特(Hayden White)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了一本在西方的学术界很有影响力书,叫Metahistory。他认为历史不应被当成社会科学,而应该属于文学。这是一个份量甚重的声明,它改变了学术界看待历史的方法。
依此可见,要想知道客观真相是很不容易的。要是在太空上有一部高清晰度的摄影机,可以穿透屋顶,几千年来不差一秒地把地球人类的所有角落里的帐前幕后的行为话语都原原本本地纪录下来,那么或许可以给我们更客观的历史答案。真希望有某个热心的外星人几千年以来孜孜不倦地在干这件事情,但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收到它给我们的意外惊喜。凭历史学家的毕生精力,是不可能回原浩瀚如宇宙的历史事件、历史细节的。其实,即使有这份意外惊喜也不能完全做到客观公正地重现历史事实。要重现历史事实,除了说和做,还要了解当事人的意愿,而意愿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是有可能与言行相背离的。所以,历史,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论证,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历史事实。正是因为如此,怀特(Hayden White)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了一本在西方的学术界很有影响力书,叫Metahistory。他认为历史不应被当成社会科学,而应该属于文学。这是一个份量甚重的声明,它改变了学术界看待历史的方法。
怀特并不是故意说一些矫枉过正的话。如果把历史当成社会科学,那么就会让人误解为历史课本,或者历史学家说的就是唯一的事实,把历史看成是盖棺定论了。如果把历史当成文学,或者说,用对待文学的态度来对待历史,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历史,这样,就可以让历史有更多种的理解空间,更多的层次和可能性。倡导这种从文学来看历史的做法的,除了一些英语文学的学者,还包括Gayatri Spivak等研究后殖民主义的学者。
了解历史是主观的,我们就可以深入探讨一些更加新鲜的看待历史的方法。这将在下一篇中继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