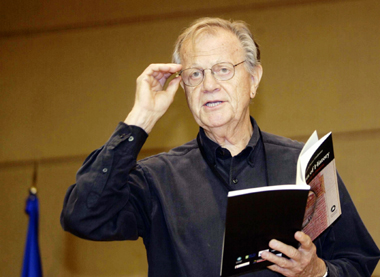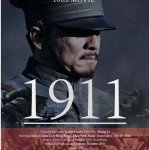日起日落,寒暑易節。時間在我們身旁溜來竄去,不知不覺我們就長大了、又悄悄然地青春漸逝,直至驀然回首雙 鬢已白。這是文學對時間的眷戀。這種對時間的感受,是將人放在無邊無際的時間的座標裡,以時間為參照來進行構思的。或者說,如果時間是數學上的無限長的永 恆的直線,那麼芸芸眾生就是這條直線上的許許多多的稍縱即逝的線段。試著換一個相反的角度,以人為參照來看侍時間。以我們此時此刻中心,我們不再是游移在 時間長軸上的線段。在時間這個維度裡,以我們的這一刻這一秒為原點,為宇宙時間的核心,那麼漫長的過去,那麼切實的現在,那麼縹緲的未來,都相應地止於或 者始於這們這一點。以這個角度來感受時間,大有文章可談。
這種看待時間的角度,不是在談科學的時間,不是愛因基坦的時間。我們這裡說的,是人類學上的時間,是精神現象學方面的時 間。什麼是人類學, 什麼是精神現象學?或者簡單地說,就是“主觀的時間”,即我們感受到的時間,而不是指科學的客觀時間。科學的客觀時間,十分鐘就是十分鐘。但這十分鐘若用 在候車亭等公車,感覺是不耐煩的漫長;如果這十分鐘用在電玩遊戲室,感覺就很短。這就是主觀的時間的一個簡單 例子。以“主觀的時間”來認識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社會,會比生硬的科學時間更加真切,更有具體的現實意義。
先說說我們的先人的時空觀。在古老的中國,道家思想,佛家思想,都強調了時間的輪迴: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時間是輪迴 的。輪迴,即是作圓周軌蹟的循環,時間的終點最終回到了起始點。相比之下,到了現代,時間則是線性的。線性,即是從落後到先進,從舊到新,是遞進式的。輪 迴的時空觀,認為過去與現在並沒有多大區別,甚至是優於現在。比如孔子,就曾追捧周代的聖人,把古人說得比今人更仁更智。在輪迴的時空觀中,時間是亙古不 變的,子子孫孫雖一代一代的交替,但社會也是亙古不變的。在線性的時空觀中,時間則是前進的,是“達爾文式”(Darwin)進化的:過去就是落後於現 在,將來就是勝於當今。在線性的時間裡,社會發展是永恆的主題。在我們這個現代化的社會裡,這種線性的時空觀主宰著絕大部分人的思維。
我們必需進一步地審視這種現代時空觀,我暫把它稱作“現代的時間”。現代的時間是一條平滑的直線,每件人和事,都很合適地安放在這條長軸上。但其 實,現代的時間並不是天經地義的。時間,其實是多重的。這是什麼意思呢?時間的多重性,意思就是:時間並不是一條由過去現在將來組成的時間軸,過去現在將 來並不是由先及後,而可以是重疊,相錯的。也即是說,過去可以在現在,現在在過去,將來在現在,現在在將來。這聽起來不可思議,但確實就在這樣的理論。我 在這裡要提及兩位歐美大學者,一位是是活躍在二戰前的德國人本·傑明(Walter Benjamin),另一位是美國學者亨利·哈倫突寧(Harry Harootunian)。本·傑明認為:時間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相互交錯的,就如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中常見的裝飾圖案(稱為arabesque,往 往是錯縱複雜的圖形,見圖)。哈倫突寧則明確地指出:歷史並不是過去,而是存在於現在。他們觀點的提法、以及他們的書,看上去深奧,但其實不然。但把本質 說明白了,就好懂了。我下面舉個例子來解釋“過去在現在”。

十九世紀中晚期的法國巴黎,經過拿破崙三世的良政和豪斯曼改造(Haussmannization), 這座大都會成為了現代化的典型,寬闊的大道,筆直的街燈,各種現代化的發明漸漸進入日常生活。現代的社科知識體係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 輩出。在那個年代,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深遠。知識階層普遍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進步的,先後經歷了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當其中的一些人類學家來到在地球 的另一個角落——在太平洋群島上,他們發現島上居民竟然仍舊過著原始社會的生活,他們茹毛飲血,拿著可笑的貝殼當貨幣進行交換。這些人類學家恍然大悟:原 來歐洲人遠逝的過去,其實就發生在眼前這些原始部落身上。或者說,這些島居民的現在,就是歐洲人的過去。
其實這並不是特殊的例子。在十九世紀未,在歐洲殖民者登封造極地干預全世界的時候,世界上各個角落的社會文化,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時間脈胳。中國是個 正在沒落的封建王朝,日本是個新興的現代社會,美洲既有歐洲殖民者的現代化,又有黑奴制度,又有殘存土著印第安人的原始社會形態,非洲、南亞次大陸繁多的 部落社會形態就更不用說了。同在公元十九世紀未這個時間點上,各種社會形態並存。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來衡量這些社會形態,則可以看出他們各自處在於不同的 時間順次。
時間的多重性,明顯地存在於在同一個社會裡。十九世紀的法國既有現代化大都會的巴黎,也有法國南部的一些社區,這些社區仍然停留在近似中世紀式的生 活方式和思維。時間的多重性也存在於我們眼前的社會。有的年輕人用最新款的蘋果iPhone, 開保時捷(Porsche);有的老年人整天在公園裡打麻將,拄著拐仗,與現代社會的技術毫不相關。這些人冒似活在同一天空下,但他們實際上是活在不同的 時間裡:這些年輕人現在的時間是在二十一世紀,這些老年人現在的時間可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同樣是年輕人,活在大都會的和活在鄉下的,他們的時間也是不 同的。這種時間的差異,往往被忽視。其實,這些時間差異,是代溝最難逾越的隔閡。
回到本·傑明的觀點,過去現在未來是相互交織的。我們現在知道了,過去和現在可以同時並存了,這是時間多重性的一方面;那麼,時間多重性的另一方面 ——未來,又如何穿越時空回到現在呢?或者說——現在,又如何越界延伸到未來呢?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概念汽車展,或者日本機器人展覽。這些未來主義的產 品,在投產之前先與觀眾見面,就是未來在現在。但更有價值的解釋,我必需延引另一個西方學界的概念,叫做“future anteriority”,我暫將其稱作“未來完成時”。
“未來完成時”是一種思維模式。未來完成時的意思有兩層:一是將來的事情將注定會發生;二是將來的事情是與現在接壤的。我舉個例子,在七、八十年代 的中國大陸,政治口號充滿大街小巷,當時最出名的一條叫做“我們的祖國將在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仔細分析這個語法結構就能發現,這四個現代化(指 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是注定要實現的,只要時間一到,就實現了。請注意,這不同於“未來時”的說法。 “未來時”的說法是:“預計在2000年實現”,或者“計劃在2000年實現”。相比之下,“將在2000年實現”中的“將”字是“必定”的意思,這種 “將實現”是沒有商量的,無可質疑的。這就是“未來完成時”。

這句口號的指向,是從未來指向現在的。這句話首先提供了一個未來的圖景:高樓大廈飛機大炮等等現代化的美好想像。接著強調這圖景必定會實現(其實是 一個假設)。這就不免讓聽者往前推理,思考為什麼現代化肯定會實現呢。然後得到答案,那是因為“現在”的原因,因為我們的現在是“社會主義祖國”,於是 “保證有美好的將來”,再推理下去,那就是要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祖國”,“奮力拼博”地做好當前的工作。 (這才是這句口號想號召的)。於是,這句口號自然地把聽者從對未來的美好幻想帶回到了現在。然後呢,聽者又會自然地從現在推到未來,他相信現在為“社會主 義建設”而努力工作、“添磚加瓦”(政治美名),就是在建設未來中的“四個現代化”。比如說,一位建築工人在砌一堵短牆當豬圈,他每放一塊磚,都似乎與那 幅未來的圖景有關:那幅高樓大廈、飛機大炮的美景,都有他這塊磚的一份功勞。於是乎,他每次看到手裡的磚,就每每看到了高樓大廈。再說了,“四個現代化” 是注定的、無可商量地會在未來具體的一天實現,那麼做好現在的工作也就是注定的,沒有商量餘地的,沒有理由不全身心投入的。這“四個現代化”的未來,非常 真切地存在於現在,被緊密地關聯到人們的日常工作中。這就是未來在現在,現在在未來。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讀者可以自己想像。我緊接著要談的是:為什麼要強調這種時間的多重性呢?依我自己的體會,這是比較特別的思維方式,我暫將其稱為 “文化人類學的思維方向”,如果你掌握這種類型的思維,就會發現思維的空間拓寬了,發現更多的日常事物之間的聯繫,以及這些事物的內在原因,因此你會享受 到更多的思維的樂趣。除此之外,時間的多重性還有沒有更具體的應用呢?答案是有的。對於上述西方學者來說,他們分析“現代的時間”,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批判 性地探討“現代性”(Modernity)。
什麼是現代性呢?現代性,是對所有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象的統稱。現代性,一般來說,開始於歐洲,然後隨著殖民主義擴展至全世 界;時間上大概是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可以簡單這麼理解,現代性就是資本主義的同義詞(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資本主義是描繪社會內裡的經濟政 治邏輯,現代性則是強調其技術及文化外觀。自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化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現代性則成為了藝術、文學、政治的大主題。現代性的看點是不斷更 新的。在我看來,在十九世紀未,現代性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包括芝加哥的摩天大樓建築,德國的汽車,巴黎的地鐵等等。二十世紀初有包豪斯(Barhaus)設 計理念,二戰後有美國的“百事可樂”,現代性在二十一世紀依然是大主題,我覺得最典型的看點包括蘋果公司產品和社群媒體等。
現代性作為一個整體,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其內容幾乎是無所不包的。太大的話題就等於射擊沒有靶子,不能有的放矢。但現代性的邏輯,卻是可以具體分析的。而從“現代的時間”這個角度來切入,是很有意義的,這樣的分析可以讓我們批判性地揭開現代性的種種迷霧。文章前面的例子提到,現代性給我們提供的時間,是一條從落後到先進的平滑直線。任何社會,都被放置在這個時間的座標上進行評估。過去的歷史,沿著這平滑的直線自然地造就了現在的社會,他們是因果關係的。這種先後有次、因果明晰的結構,是現代性時間給予我們的“時空觀”,並且讓我們相信它是天經地義的,無可辯駁的。
然而,時間的多重性,就是對“現代的時間”的否定。這種否定有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牛頓的時空科學架構的否定。人們曾認為天經地義的時間,在愛因斯坦那裡就成為了一個可以延長縮短的維度。同樣的,我們早已習慣性地認為,各個國家的現代化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我們都在往同一個方向發展,我們的技術,我們的現代社會在不斷地進步。但時間的多重性,就是對此提出質疑,認為事情並不都這樣。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說,“世界潮流,浩浩蕩盪,順者則昌,逆之則亡”。這個潮流,就是現代性。這種潮流,讓許多人相信,現代的生活、現代的思維更加美好。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把現代性看作標準,將其當作使命和歸宿。他們都沒有批判地接受了“現代的時間”。在二十世紀初,人們這麼想是有其實際意義的;但在我們這個後現代主義的時代,這是值得審視的。
我們經常時常聽到類似這樣的論調:那個非洲國家,落後人家五十年。意思就是說,那個國家停留在五十年前的現代化水平,是落後的,它有必要趕上來,和大家保持一致,達到當今的標準。這種“有必要趕上來”,就是“現代的時間”在行使其統一世界的功能。在無孔不入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下,這個國家確實有必要趕上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想,事情並不是這樣黑白分明的。我們人類的社會,是很多元的,在歷史上,每個社會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生命觀。然而,當歐洲殖民主義者開始作全球性的市場開拓,各個完整的古老的傳統社會形態,就漸漸被現代性打破了。在短短的一百年間,這些幾千年幾萬年的古老的生命觀,就突然被現代性覆蓋了。那些衣不蔽體、為了幾個破貝殼大打出手的太平洋島民,在短短幾代人的功夫,就穿起了西裝用起了蘋果電腦。他們的祖先,幾千年幾萬年來,無非就是捕魚填肚子和找個異性生幾個孩子,閒時再曬曬太陽,有必要時再拿幾根尖尖的樹枝去打臨近的部落。時間,對他們來說,就是周而復始地做這些事情,世界很簡單。突然間有一天,他們有了使命,必需要現代化、要發展、要開發、要去除“落後”的傳統向“先進”看齊,要去除“不文明”的“原始”的行為,學習“文明”的生活方式。緊接著,他們又很快地發現,他們的現代化水平,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的國家,他們要趕上來。於是,他們的生命,就籠罩在“現代的時間”的魔爪之下。

在這裡要注意,這種“要趕上來”的時間是別人給他們的,而不是他們自發形成的,這個轉變的過程是非自然的。這些古老的社會,在外力的作用下,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時間活了(這很像亞當和夏娃(Adam and Eve)的出樂園(Garden of Eden)),他們成為了那條光滑的時間長軸上的線段。 “現代的時間”就這樣抹殺掉各種社會的不同的時間,完成了對世界的統一。現在的人們,都活在這個時間體系裡,無從逃遁。而且,這種時間的抹殺和改寫,是不可逆的。一但被改寫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們是絕不會放棄舒適的海濱別墅去住荒山野嶺的山洞的。
雖然我們不能逃避現代的時間,但對其進行審視卻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有積極作用的。現代性,是一種時空觀,應看作是一種哲學,一種信仰,一種生活方式。在這裡我強調“一種”,意思即是還存在“其他種”。用時間的多重性來否定“現代的時間”,絕不是否定現代性的內容和意義,而是否定現代性天經地義的性質,否定其唯一性的合法存在。多重的時間,讓我們在這個法西斯式的“現代的時間”魔爪下,定位出那些已失去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不可能也不想要顛覆現代性,而是想幫助我們解決一些現代性問題。比如哈倫突寧以及其他不少學者,就拿時間的多重性,去反駁傳統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觀。他認為現代性是多極的,各個現代國家都有同樣重要的貢獻,而不是由歐洲人統領的。 (這將另作文章論述)
寫到這裡,我算是講完了。有一天,我對一位年長的朋友麥克提起這些觀點。他打斷了我的話說,“我要補充這些觀點。我認為時間是——不存在的。”然後解釋了一通。我覺得很有意思,於是把他說的話進行再創作以適合中文的語境,供讀者們參考。我暫且把他的意思起個名字,叫做“存在主義的時間”。
我們認識的時間,是一段一段的。時間這個詞,是由“時”和“間”組成的。 “時”即是時刻,是一個點;“間”的意思是“段”的意思。 “時”和“間”合起來,就是指“時段”。我們感受到時間的存在,其前提是因為我們感受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就是感受到“時段”的存在。我們常說,“我太忙了,我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這裡的“時間”顯然是指一個“時段”,是一個“過程”。但“存在主義的時間”卻是把時間當作一個“點”,當時間成為了點,時段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說,我們就感受不到時間的存在了。
如何把時間當作一個點呢?最好的例子是掛鐘。你不妨看一看你牆上的鐘,仔細觀察秒針的移動,或者鐘擺的來回擺動。秒針和鍾擺每移動一次,就發出一個滴答的聲音,我們就過完了一秒。緊接著,秒針又進入下一秒,然後再下一秒,再再下一秒。在永恆的讀秒中,過去的一秒是不存在的,未來的一秒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永遠只有現在這一秒。每一個滴答,就是一個現在。我們常把鐘錶當作計時器,我們會累加每一個滴答:“一秒過去了,兩秒過去了,三秒,四秒……”我們習慣於把時間看作是一段一段的。但實際上,那根移動的秒針的客觀意思是“現在的一秒,現在的一秒,現在的一秒,還是現在的一秒……”永遠都是指向一秒鐘這最基本的時間單位,這個點。這就是存在主義的點的時間。在這個永恆的“現在的一秒”的時空裡,過去和將來形成的“時段”是不存的。過去的時間和將來的時間,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中,而不是客觀存在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時間是一種現代文明的文化虛構。過去和現在,是一種現代文明的文化虛構。我們回顧過去,憧憬未來,就是不願停留在現在。我們的生命 意義,都是在過去和未來的想像中構造出來的,而不是立足於現在這一秒;我們總是掏空現在這一秒,將其歸入過去或者併入將來。遠古的人類社會,是沒有多少時 間概念的,只是到了現代文明社會,時間才如此明確地變成了具體的主宰,變成了駕馭我們的上帝。我們都活在有限的時間裏面,人知道自己終將要死去,以死亡的 終點時間作為所有事情的支點,作為所有事情的公約數,那麽所有的事情就變得有了這樣那樣的意義。這些意義的探討,成為了哲學的思考,再細分成為其它的學 科。如果人真的能長生不老,那麽許多事情都不用在乎了。
我想建議您思考一下我說的這些理解時間的角度。或許在忙忙碌碌的每一天中,停留片刻,把注意力放在“此時此地”(Here and Now),給自己的時間一次喘息的機會,呼吸一次“現代的時間”以外的空氣,不要完全被“現代的時間”所蒙蔽,勿勿地過完這忙碌的現代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