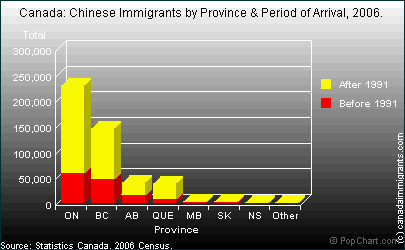文|東東
在很久很久以前,寒冷的冰川已經消失,歐亞大陸東部一片郁郁蔥蔥。在山林水邊的某個好地方,住著某一群山洞人。他們像許多穴居動物一樣三五成群地住在大大小小的山洞中。洞外的近處有平地、中處有湖、遠處是高山峻嶺。太陽總在東邊升起,在西邊落下。
卡卡是其中一個小夥子。他身體結實、下巴雄厚,最擅長捕野兔,業余愛好是撿石頭,然後搬到小洞裏送給娜娜,討她歡喜。娜娜其實真正喜歡的是卡卡的下巴。她和卡卡住在一起,說話少干事多。她擅長的技能是採集,在最荒蕪的季節也能采摘到好野果子和稻草,而且這些果子吃了十次有八次不拉肚子,很好信賴。她不但與卡卡分享果子,也與其它山洞的鄰居分享。卡卡和娜娜都不知道自己多少歲,只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就像一棵開花的樹,該結果子生孩子了。
但孩子是怎麽來的,這個問題一直困惑著卡卡。卡卡和娜娜有一個一歲大的孩子。卡卡知道這個孩子是從娜娜肚子裏爬出來的。但是,那個小肉球最早的時候是怎麽鑽進去娜娜肚子裏的呢?卡卡想:它總得先鑽進去,在裏面慢慢變大,然後才能爬出來。卡卡想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
一條絹流從卡卡和娜娜的小洞裏流過,在洞口的左邊水簾洞之下住著二男二女,其中一個男子是歪下巴,有一個女子是短下巴。這是卡卡不喜歡他們家的一個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卡卡妒忌這一家的小孩。卡卡和娜娜家只生了一個小孩,而歪嘴家則有十來個小屁孩。這些小孩都很粗壯野蠻,大一點的小孩子手臂長得跟蟒蛇一樣長,頭發像樹藤一樣粗;那個二歲大的小孩,臉上的胡子已經像娜娜一樣濃密。他們的手腳敏捷,就像是峽谷河道拐彎處那片樹林裏的猴子一樣多。有一天,他們成群結隊地衝上山坡,無意間發現了卡卡的一個秘密。勤勞的卡卡將近來找到的石塊放在一個大樹洞裏面,這幾十塊天然的石頭是最高品質的——石塊大小適中,形狀各異,有尖的、有扁的、有圓的,甚至有蝴蝶型的。卡卡的計劃是:秘密地把這些石塊攢著,然後在同一天裏拿回洞裏,給娜娜一個大驚喜。沒想到驚喜倒是先給了這群鄰家的小屁孩,他們見到有石頭就衝上去搶。卡卡揮著一條又長又粗的樹枝檔在石堆前面,張開大下巴,把牙齒磨得絲絲作響,把眼睜瞪大如餓狼,也沒能把他們嚇走。他能擋住跟前的兩三個小孩,但擋不了其他同時衝過來的七八個。卡卡發現身後的石塊已失守,就轉身去追已搶到石塊的小孩,剛才被擋住的小孩即乘機也搶到了石塊。卡卡勢單力薄顧此失彼,不一會,所有石塊都洗劫一空。卡卡望著這群毛手毛腳的“盜賊”揚長,無可奈何地把樹枝甩在地上,然後像一攤泥一樣無力地蹲在地上,埋頭嗚嗚的哭。哭完了他就開始幻想自己有許多的小孩,這些小孩漫山遍野,像蝗蟲一樣,所到之處,把所有的石頭收拾得片甲不留。在幻境裏,他站在山頂看著,松開下巴哈哈地笑,而鄰家那群小孩攤坐在地上哇哇地哭。他想得高興,就擡起頭張開眼,卻望著四周空空如也,不但身邊一塊好用的石頭都沒有,剛才頭腦裏的那群自己的小孩也一個沒有看見,只有草叢中一只蛤蟆和他四眼相對,他于是又埋下頭去繼續傷心。
卡卡回到家,唯一能夠做的報複,就是恨恨地在洞裏的小溪裏“唏唏”和“呸呸”,即是撒尿和吐口水,讓那混濁的髒東西順水流到下面的水簾洞去。想了想,還是不解恨,于是在水裏“噗噗”,也就是大便。沒料到那大便塊太重,竟然不隨水流下去,倒是賴在山洞的水底裏不動,那臭氣倒嗆著了自己。娜娜也捂鼻子,但她從不責怪卡卡。她默默不作聲,拿了根小樹枝,很認真地去挑那幾塊屎,那幾塊東西才隨著水滾流了下去。卡卡見狀破涕爲笑,娜娜也看著他縛緊的臉笑開了,也“撲哧”一聲笑了。卡卡見到娜娜在笑,“咔咔”地笑得更厲害了。笑聲中,他搶過那樹枝,在水裏比劃著,然後抱著肚子,笑翻在地。兩個人的笑聲在山洞裏的回音壁繞來繞去再地傳了出去。水簾洞下的幾個小屁孩依稀聽見,探頭探腦來看究竟,並不知這笑聲與自己有關。
報複是治標不治本。卡卡很清楚根本的解決辦法是讓娜娜的肚子鼓起來,生許多許多的孩子。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娜娜的肚子就沒有鼓起來過。于是,卡卡必需弄清楚這孩子是怎麽鑽進去的她的肚子裏的。
卡卡先是試著回憶自己當初是怎麽鑽進去的。他記得昨天他在小溪裏用削尖的木條刺中了一條魚,又在沼澤裏捉了幾只青蛙;前天,他和若幹男女聚在一起跳熊舞、殺了幾只山豬放在山頂的草堆上燒掉,祭祀山神;再前一天,他什麽事沒做,只是躺在地上想事情;再再前天……他就這樣一天天地往前想,期望想到他剛出生的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想到第十天的時候,卡卡就睡著了。在第二次的嘗試中,他找些苦葉子嚼在嘴裏,讓自己清醒。想到第十天的時候,手臂上被蚊子咬了一口。他拍死了蚊子,思路卻隨著“拍”的一聲就斷掉了,氣得他不斷地辱罵蚊子,罵完了又只好重新從最近一天開始想起。他如此反複總是一無所獲。卡卡于是嘗試跳躍式的思維,他記得很久以前,他比一只小羊還矮的時候,有一天地動山搖,所有的大人都嚇得跪在地上求饒,他們不知做錯了什麽事,讓山神動怒了。卡卡無法記得比這件事更早的內容了。因爲這個回憶太恐懼了,卡卡于是取消了這種做法。
卡卡去問別人。除了水簾洞下面的男女,他逢人便問。有人說是孩子是從高山峻嶺的另一邊的一些石縫中來的;有人說與蛇有關,說是女人與蛇在夜裏相遇,第二天都要生孩子。幾年前卡卡的姐姐被蛇咬了,不但沒有生孩子,倒是在第二天就死了。可見此話不可信。會不會與大樹有關?卡卡記得,在自己的兒子出生之前,他和幾個夥伴一起去過砍樹。那樹杆很硬,用石塊切割半天只切入一條細痕。卡卡用力過猛,結果反而把自己的手給切破了。他又痛又氣,扔掉石頭對著大樹跺腳揮拳大喊大叫。也許,卡卡想著:朝大樹大喝大叫與生小孩有關。于是他在林子裏找了一棵與記憶中類似的樹大叫大喊。把樹上的烏鴉都嚇飛走了。回家一看,娜娜的肚子仍是平的。卡卡並不放棄,他回到林子裏嘗試了其他品種的樹,然後再選擇同一品種但不同大小的樹。他嚷到喉嚨沙啞,下巴酸痛,但回家一看,總未見成效。
會不會與祭祀的舞蹈有關?每個月圓的傍晚,所有山洞人都到林子中間的空曠地會聚、圍著火堆跳舞。山洞人大多數會跳虎舞、熊舞、狼舞、老鷹舞、鹿舞。卡卡因爲打獵活動範圍大,見多識廣,所以發明了鳄魚舞,甚至還有山豬舞。但哪種舞與生小孩有關呢?卡卡留意到那水簾洞的二男二女將鹿角綁在頭頂跳鹿舞,他于是也開始鹿舞。他找來幾把彎曲有致的樹枝,用雙手拿在頭頂佯裝鹿角,屁股後還夾著一條藤條當鹿尾巴。他不停地擺弄身體,直跳到火堆燃切,衆人散去,他仍然不願停下來。月光下塵土飛揚,他一個人在曠地上蹦來跳去,口裏“哇哇”學鹿叫,臉上裝出各種古怪的表情。住在水簾洞裏的兩個小孩躲在暗處偷笑,但被卡卡發現。卡卡龜下腰,挺著頭頂的樹枝爬衝過去,把小屁孩嚇得四散而逃。
直到跳盡了力氣,卡卡才撇下樹枝和藤條,氣喘呼呼地趕回洞裏去看娜娜的肚子。可是娜娜的肚子仍然沒有動靜。卡卡的執著態度感動了娜娜,她很希望自己的肚子有所動靜,好讓卡卡開心。看著卡卡整天辛苦地奔波,她也感到焦急。但是事與願違,肚子平靜得像沒有風的午後山坡上的大石塊。幾天後的一個早上,她突然發現肚子裏傳來輕輕的天空行雷滾動般的聲音,她趕緊跑出洞去,把在空地上獨跳鹿舞的卡卡拉回洞來。她指著自己的肚子,欣喜若狂。卡卡來不及把鹿角從頭頂解下來,就把耳朵貼在娜娜的肚皮上聽,娜娜默默不作聲,讓卡卡聽了幾個小時。那不是小孩的聲音,那是娜娜吃了一只青蛙後消化不良的緣故。
卡卡經常在半夜夢見小孩。他很想把夢中的小孩抓幾個出來塞進娜娜的肚子,可是他做不到。他剛想動手抓,就醒了。一醒了小孩也就頓時不見了。想必他們在黑暗中躲起來了?他坐起來環顧小山洞四壁的角落,但夢裏的孩子一無蹤影,只看到洞口有月光射進來,幾只熒火蟲繞著垂下來的藤蔓飛舞。卡卡失望地歎了口氣。娜娜被他的動靜吵醒,也坐了起來。她知道他又是爲了孩子的心事。她伸過手來安撫卡卡粗壯的下巴。卡卡夢想破滅、委屈得正想哭。娜娜溫柔地將臉貼到他的耳邊,輕輕地問:
“囑囑?”
卡卡收回哭意,點頭“嗯”了一聲。娜娜伸長了嘴湊過來,在卡卡下巴的胡子中蹭來蹭去,就像鴨子的嘴在草叢中覓食似的。卡卡總算平靜了下來,很快就睡著了,白天的大喊大叫和鹿舞把他累壞了。
會不會是不是與芒果有關?水簾洞裏那個歪嘴男子的經常啃芒果,吃剩的芒果核堆在洞口像長毛象(猛犸)的屎一樣高。卡卡于是找來許多芒果,不管酸的甜的都往嘴裏送。胃裏很快就受不了嘔吐出來。他把那些穢物敷在娜娜的肚皮上,期望奇迹的出現。娜娜覺得那東西又酸又臭,髒髒的癢癢的很難受,幾次想用手弄掉,但都被卡卡止住。最後一次卡卡生氣了。他甩下娜娜的手,索性蹲到山洞最裏面的角落,雙手交叉抱住膝蓋,嘟著嘴,一語無發,雙眼呆呆地盯著空地看,一動不動地就象塊石頭。娜娜後悔自己的行爲了。她理解卡卡生孩子的心切。她默默不作聲,輕輕地走到角落蹲下來,挨著卡卡。卡卡假裝沒看見,眼睛數著洞壁上的螞蟻;娜娜臉上靜靜流下兩行眼淚。他們就一直默默地蹲著。後來穢物風幹後自動脫落,頑固的肚子仍然沒有變大。
大概是那月亮。卡卡想,那月亮的肚子有時塌下去,有時鼓起來,有時鼓得圓圓的亮亮的,就像是娜娜曾經有過的肚子。所以,月亮裏面肯定裝滿了許多孩子。要是能夠得著,把月亮的肚子扒開,那麽要多少孩子就有多少孩子。可是月亮太高了,爬不上去,于是他就朝月亮扔石塊。他想:要是能扔中月亮,觸動了月亮,娜娜的肚子就會像月亮一樣鼓起來了。他很滿意自己的觀察分析能力。他還注意到,月亮有時遠有時近,和他捉迷藏。譬如說,在空曠地上,可以看清夜空中月亮的位置,可以輕易地瞄准,可是月亮躲得高高的,即使挑了較輕的石子,也不可能扔得著。當他走進樹林,發現月亮其實躲在密密匝匝的樹枝葉的背後,它的高度還不及樹頂,是石子可以夠得著的範圍。但問題在于月亮被樹枝擋著很難瞄准,石塊往往是扔到了樹上。卡卡不斷地變換位置朝月亮扔石頭,一會兒在樹林,一會兒跑到曠地上。他希望以此來迷惑月亮,要是月亮稍一疏忽,在空曠地忘了撥高空中,就可以扔到了;又或者月亮藏到樹林時,忘了選一塊沒有樹擋住的地方,那石子也可以扔中月亮。但是,不管他如何變換地點,狡猾的月亮從不出差錯。卡卡並不服輸,他不斷尋找新的樹林和曠地,跑來竄去,越跑越遠。他越了湖,接近了遠處黑壓壓的高山。山的峭壁有一只矗立的狼仰脖長嚎,月亮嚇得躲進雲層,四周驟時漆黑一片。
娜娜每天采集果子,按時回洞。卡卡每天打獵,比娜娜稍晚一些回洞。娜娜在洞裏沒事幹,就在兒子身上捉虱子。一般來說,捉到第九只虱子的時候,卡卡就回來了。可是這晚捉了十七只虱子,也不見卡卡的蹤影。她心裏掠過各種不祥的懲兆。不久前,在湖邊專心采集的時候,一頭路過找水喝卻不長眼睛的長毛象,把她的一個同伴踩死了。而且,她聽說高山裏有各種凶殺的動物,它們一口就可以咬死一個離群的人。她越想越可怕,趕緊改變想法。或許卡卡鹿舞跳得太多,變成了一頭公鹿,去找他的母鹿去了。娜娜這麽想,又或許他的大下巴迷住了遠方的山洞女人,于是在她那裏過夜了。再或許是卡卡不滿意自己的肚子沒有變大,離棄自己了。不管哪種猜想都讓她睡不著。天微微亮,她就奔走各個山洞中向鄰居報告危機。于是,所有的洞人展開了地毯式的搜救行動。在太陽正當空的時候,他們終于在高過人頭的草叢中發現了卡卡。最先發現卡卡的是水簾洞中那個嘴歪得最厲害的兒子。他撥開草叢,只見卡卡四腳朝天,一動不動,大下巴張開著,嘴上面一群蒼蠅飛飛停停。這小孩不敢走近,拿了一根長樹枝地去桶卡卡的屁股,試探他的死活。娜娜聞聲而來,見狀心裏一緊,大喊一聲撲了過去,還來不及哭就發現卡卡還活著,他只是昏睡過去。他那張大的嘴巴正打著呼噜,是牙縫中的殘肉引來了蒼蠅。水簾洞的一個嘴不歪的小孩撥了根細草伸進卡卡的鼻孔,卡卡打了個嗆但仍然沒有醒。原來,昨晚卡卡瘋狂地追逐月亮、跑得精廢力盡的時候才發現迷路了,偏偏被狼群發現和跟蹤。他就繼續跑,跑盡了最後一絲力氣,他跌倒了爬不起來。他聽見身後狼的叫聲在逼近,知道要死了。說時遲那時快,他趕在被狼咬之前睡著了。他以爲人一睡著就沒有知覺了,那麽被咬時就不痛了。這一睡倒救了自己一命。一只餓熊把狼群趕跑,想要獨吞獵物。它在卡卡跟前嗅著,以爲他已死了,悻悻離開。卡卡于是在睡覺中死裏逃生,此時仍在死死地昏睡著,生怕醒來會痛。不管娜娜擰耳朵捏脖子,他都拒絕醒過來。大家哈哈大笑,但又啧啧稱奇,不知道卡卡如何在狼群出沒的險惡夜裏活下來的。最後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擡回小洞裏。
不知道睡了多久,卡卡才鼓足了勇氣醒過來。他睜開眼,想看看自己被狼咬後,身體還剩下多少塊。沒料到自己竟還完整,眼前是關切的娜娜。他不禁高興得跳起來哇哇大叫,緊緊抱住娜娜。回過神來,他發現娜娜的肚子仍是平平的,不禁又哇哇大哭。娜娜很心痛,緊緊地抱住他的下巴,卡卡則像小孩子一樣,發著脾氣哭鬧,拍打著娜娜,口裏埋怨著她。娜娜默默不作聲,任他拍打。過了一會兒,卡卡哭鬧完了,娜娜幫他揉揉背按按肩,舔他大腿上被草石劃破的傷口,卡卡仍喘著粗氣。娜娜按摩著卡卡的下巴,輕聲地問:
“囑囑?”
卡卡點頭“嗯”了一聲。于是娜娜又伸長了嘴在卡卡的胡子中遊走,就像是在草叢中尋找卡卡的下落。卡卡的胡子被蹭得很舒服,身心慢慢放松下來,昨夜的勞累、恐懼和怨恨,漸漸被蹭掉了。剛才那個哭鬧的“小孩”,變成了聽話的“小孩”。
“賊賊?”
娜娜柔聲問道。卡卡又點了點頭。娜娜于是把卡卡藏到自己秘密又溫暖的地方。那晚,卡卡睡得非常輕松和踏實。他沒有再夢見小孩。第二天早上,他決定從此不再做無謂的努力了,不再去想娜娜的肚子。他要珍惜娜娜。他要去找些石頭送給她,哪怕是要跑到高山峻嶺的另一邊,哪怕是要穿過狼群越過虎地,他都願意。
經曆了生死劫的卡卡,從此變了。他不再傻乎乎地衝動做事了。他時常保持著冷靜的頭腦及懷疑的態度,並因此漸漸贏得所有山洞人的敬重。另外,有傳言稱他有神力,連狼群都怕他。這也幫助提高了他的聲望。水簾洞的小屁孩從此不敢偷他的石頭,而是去偷別家的石頭,然後爭寵地獻給他。
兩個月後,沒料到的好事發生了:娜娜的肚子漸漸鼓起來了。娜娜告訴卡卡,卡卡並不相信,笑她又是吃了青蛙了。又過兩個月,娜娜說 自己有孩子了,卡卡仍然不信。他繼續取笑她說,當她盤腿坐的時候,越來越像鼓著氣的青蛙。又過了兩個月,娜娜的肚子更大了,卡卡仍然不信。他認爲娜娜吃了一只帶殼的大烏龜,是那硬殼把肚子撐大了的。再過若幹個月,一個血茸茸的東西從她肚子裏鑽出來了。卡卡定睜一看,發現那團東西竟然不是一只烏龜,而是一個小屁孩,這才相信了。他又驚又喜,端祥著這個意外的東西。良久,他突然明白過來了,“咔咔”地大笑。娜娜問他何故。卡卡笑自己的愚蠢,他說,娜娜生孩子與他吃芒果無關,與他大喊大叫無關,與月亮無關,更加與他跳的鹿舞無關。
終于找到了答案了。卡卡鄭重地告訴娜娜,答案就是鳄魚舞!卡卡解釋說,十多個月前,在他迷戀上鹿舞之前,他跳過不少鳄魚舞。他指著孩子的下巴說:看他長長的下巴,多像是鳄魚的嘴。
卡卡決定將這個重大發現公諸于衆。有鑒于卡卡的威信,山洞人都深信,鳄魚會促進生育。水簾洞的歪嘴男子也站出來以自例爲實證:稱自己家孩子多,全拜鳄魚所賜。他說,雖然他打獵從沒見到鳄魚,但是小時候聽過老人講鳄魚的故事,至今不敢忘,于是才有這麽多孩子。信男信女聽後更加深信不疑,紛紛在自家的山洞石壁上刻畫了鳄魚的輪廓。但都畫不好。他們擔心,萬一不小心把鳄魚畫歪了,生出來的孩子就會像水簾洞的歪嘴男子。所以,他們紛紛要求卡卡爲公衆畫一條標准的鳄魚,至少他見過真品,而且他的下巴很端正。
卡卡深感責任重大,知道這幅畫事關族人興衰,所以不敢怡慢。他從小山洞中幾百塊珍藏的石塊中精挑細選,小心翼翼地拿出了最好的石刀,在曠地的一棵枯死的大樹樁上刻下了鳄魚的永久形象。
從此,每到月圓之時,男女老少就到樹樁前膜拜,圍著火堆跟卡卡學跳鳄魚舞。地上的人們發出“咔咔”的鳄魚咬牙的聲音,天上的月亮靜靜地聽著看著,照樣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
2014年5月10日